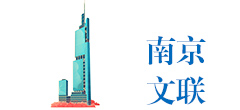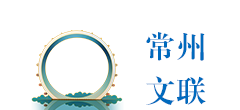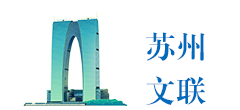文 | 张丹
贾樟柯电影《风流一代》将“俱往矣,不回头”作为宣传语,事实上,影片正是在不断“回头”中完成了一次千禧年以来的尽情回望,呈现出一种基于“人”的立场,记录人民集体记忆与情感结构的时代镜像,在银幕上构筑了一部关于普通人的生活史与心灵史。同时,弥足珍贵地激活二十余年间的集体记忆,在银幕上与观众,尤其是时代的亲历者完成了一次历史重返与跨时空对话。
《风流一代》以“拾得影像”(found footage)形式大量引用导演本人前作的情节、人物,与二十余年间不间断“持数码摄影机”形成的影像素材共同构建,虚构与纪实的组织,以及堪称“数码影像史教材”的异质画面并置,使影片呈现出超乎寻常的实验性与互文性,并试图以此证明——芸芸众生的挣扎与奋进、坚守与希望,才是这个时代最真实、最动人的诗篇。

一、从个体经验到时代缩影:叙事性、互文性与人民性
研究者认为“拾得影像或称既得影像,是对已有的影像文本进行发掘、重访,并可基于与原作全然不同的创作意图对既有的影像进行挪用、拼贴与重塑的影像生产方式。”《风流一代》便是拾得影像的一次积极实践,在叙事部分,2001、2006年的故事主要引用自《任逍遥》《三峡好人》《江湖儿女》贾樟柯导演本人创作序列中的作品,与2022年全新拍摄的部分接力铺陈,共同构筑叙事主线,补充纪实影像缺失的人物关系,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正如导演所言,“故事片更容易拍到存在于人际关系中的真实。”故事在重复中创造,生发出一种强烈的对于普通人个体命运的关切。
2001年的大同,无名的人们有着无比清晰的面孔,他们热衷于唱歌、跳舞,有着与灰色、静默空间截然相反的喧哗,这正是影片叙事主体人民性的体现,镜头聚焦于下岗工人、小商贩、务工者……歌声、舞蹈是无声处的“有声”,是失语者的表达。故事以巧巧、斌斌为表述对象,凝视二十余年来个体生命的生活变迁与精神漂流,记住了他们在历史潮流中的出走与重返、调试与挣扎、困顿与坚守,真正使普通人回到历史的主体位置。
《风流一代》一如既往地塑造了平凡而鲜活、坚韧且富情义的女性形象,她的平凡而珍贵,执着的情感坚守,置身困境时的扶持与对生活的热忱……正是这些朴素的情感与价值,构成了人民精神世界的基石,使他们能够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保持内心的平衡与尊严。世纪初的巧巧正当青春,她是《任逍遥》《江湖儿女》中的巧巧,如同衣服上刺绣的蝴蝶,身着招摇的服装,舞蹈般轻盈地穿行于商演舞台、歌舞厅和穷街陋巷,有着与时代浑然一体的热烈。《任逍遥》《江湖儿女》有过介绍,巧巧、斌斌们是下岗一代的子女,青春正当时的他们“浑身有力气而无事可做”,大同所代表的枯竭、颓败的家乡是渴望挣脱的地方,斌斌告诉巧巧,“我想走,出去闯闯”,如同《风流歌》写下的那样:
“我希望生活过得轰轰烈烈,我期待事业终能有所成就。
我年轻,旺盛的精力像风在吼,
我热情,澎湃的生命似水在流。”

五年后,巧巧南下奉节寻找杳无音信的斌斌,昔日不停换装、戴假发的巧巧,已成为一件鹅黄色衬衫、一条灰色裤子便可行走数日的素面朝天的中年女人。那个曾被斌斌阻止,十一次哭泣着反抗的她已在岁月的磨砺中成熟,她执意寻找避而不见的故人,只为了“有些话要说清楚”,“这么长时间没消息,不放心”,对她来说,跨越万水千山的寻找背后的驱动力不止是爱情,还因为“不放心”,昔日的热烈和挣扎已悄然褪去,唯有一份深藏于心、难于割舍的牵挂。
2022年,斌斌拖着病体回到大同,这是自“江湖”归来的斌斌,“外边没甚好干的,租房吃饭,都得花钱,还是家里好,最起码有套房”。十余年间,大同经历了令人瞩目城市改造,古城换新颜,高楼林立、街道宽阔。故乡对斌斌而言,仍拥有庇护的力量,如于坚评述费里尼电影所说,“格蕾丝卡就是故乡, 女人是我们时代离故乡最近的”,在贾樟柯电影中,巧巧便是故乡。
在表征全球化与消费主义的沃尔玛超市,斌斌与巧巧重逢了,他摘下口罩,露出那张过于斑驳、衰老的面孔。两人在冬夜的街头同行,年轻的恋人们擦肩而过,手中的星巴克,远处的麦当劳与直播手机装饰着中国数百座城市的街景,唯有夜色中矗立的宇航员雕塑提示着,他们正站立于出生的土地,曾经的热烈、执拗在岁月磨砺中化为面对生活的韧性。抚慰人心的是,故事的最后,巧巧蹲下身去为斌斌系上了鞋带,这与《江湖儿女》中她照顾回乡的斌斌一样,是一份对故人的“情义”,也是对往昔的珍重,她换上了运动服和荧光臂带,汇入年轻人中与新时代同行,这何尝不是对“风流一代”最朴素、最诚挚的祝福。
每一代都有自己的“风流”,“风流一代”是正在老去的一代,却不代表历史的退场,影片以逼近现实的最大努力,展现了他们的来处与去向,记住了生命的尊贵。

二、“复活的艺术”:纪实性、细节性与日常性
早在《二十四城记》中,纪实与虚构影像的并置已经被实践,“历史就是由事实和想象构筑的”,贾樟柯用电影的形式表达他对历史的理解。相比而言,《风流一代》更具探索性,纪录部分的“事实”除了对剧场承包者的短暂采访之外,叙事完全被置换为人与细节构成的抽象情绪。
随时间进程同步拍摄的影像仿佛幽灵,引领人们游历时间的河流,2001年数码摄像机拍摄的画面带着粗粝的质感,2010年的影像则呈现出差异的技术特征,直至2022年最新拍摄的片段……每一种影像质感的差异本身就成为时代变迁的见证。这是影片最为动人之处,影像、声音来自历史现场,而非重塑,“真实”复活了人们的集体记忆,“风流一代”重返午夜梦回的岁月,年轻一代与记忆中年轻的父辈重逢……每个人都能看到过往生活的痕迹,使之具有强烈的情感动员力量。

《风流一代》正如其名,讲述的是人,准确说是一代人,纪录影像承载了个体生命碎片化、偶然性的历史经验,“新世纪第一个春天”,女人们在张贴着“旭日升”冰红茶广告的屋里围着火炉歌唱、工人们在工厂改制前合影、路人在闹市匆匆行过、移民等待迁徙、乘客戴着口罩……如同福柯描述的“无名者”,“他们应该属于那些注定要匆匆一世,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的千千万万的存在者。”他们的表情充满时代特有的扭捏、迷茫或紧张,表情被放大,个体生命被看见、被记住,成为时代最真实的注脚。他们生而为人“有血、有肉”,有一颗心,“会喜,会愁”,影片片名来自纪宇的长篇抒情诗《风流歌》:
“风流哟,风流,什么是风流?我心中的情思像三春的绿柳;
风流哟,风流,谁不爱风流?我思索的果实像仲秋的石榴。”
2001年的影像裹挟着扑面而来的新世纪气息,未来主义雕塑以宇航员脱离地球的姿态,充满整个民族对现代化追求的向上之力,这正是新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普遍心态的真实写照与精神象征。文化宫犹如一座被废弃的、庞大的容器,接纳“困在浪潮中”(caught by thetide)的人,打发时间的退休老人、谋求生计的下岗女工……与2006年奉节的废墟如出一辙,生动展现现代化进程的复杂面向。
从2001年大同的歌舞升平,到2006年奉节的断壁残垣,再到2022年改造一新的大同,人物与城市的变迁相互映照,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人物之间那种基于人性的关怀始终不曾改变,他们超越孤立的个体,成为时代的缩影。

正如贾樟柯所述,“生命的尊贵在人海里面,你只要去注意每一张面孔,你就会注意到每一个有尊严的人。”《风流一代》是一次对普通人生命价值的致敬,它提醒我们,历史的创造者是亿万普通人民,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最真实、最动人的风景。当电影落幕,他们的面孔在观众心中挥之不去,或许没有留下名字,但这些表情与融入时代记忆的生命经验已在银幕上留成永恒。
作者简介
张丹,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
来源: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