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提出、溯源及再思考
文 | 潘浩
在2025年的中国文艺理论界,《延河》杂志提出的“新大众文艺”概念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延河》杂志上一次引起极高的关注度还是1958年,时隔60多年后,《延河》以敏锐的文艺嗅觉凭借“新大众文艺”的概念再次引发关注。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引发文艺界持续深入的讨论,在于它与当下文艺生态的深度共鸣,对“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探讨也是对当下文艺生态的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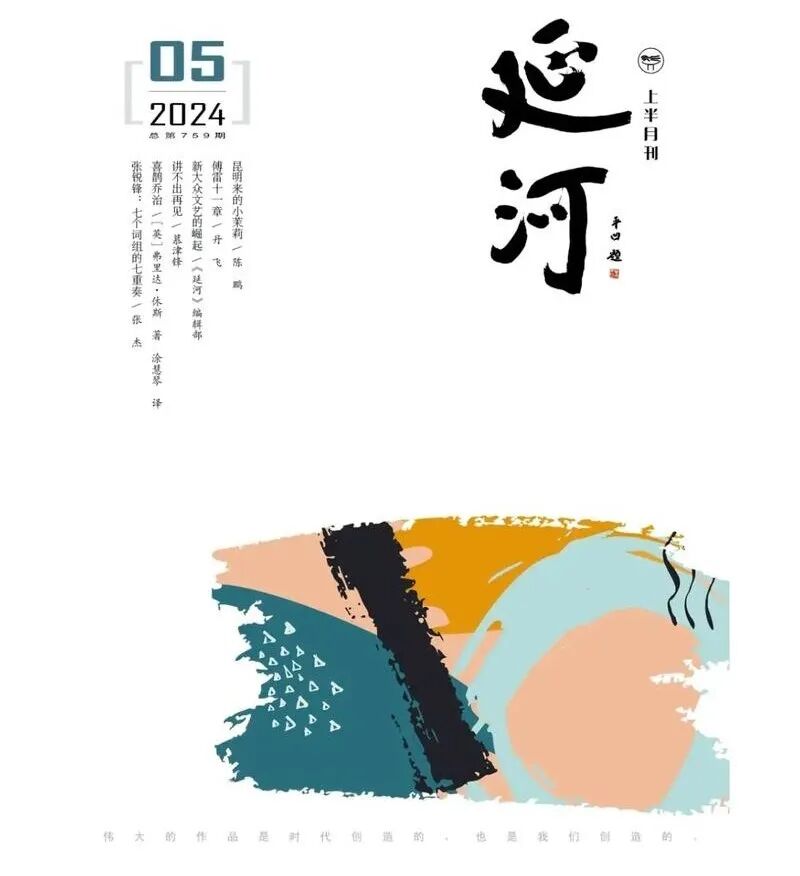
一、“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提出
2024年第5期的《延河》杂志首次提出“新大众文艺”的概念,为理解数字时代中国文艺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理论抓手。2024 年第7期《延河》发表理论文章《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文中对“新大众文艺”的概念作出了界定:“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2025年第7期的《延河》杂志以大众文艺大展专号的形式亮相,刊登了郭德纲、俞敏洪、邓亚萍、张越、周洲等众多文艺名人的文章。2025年10月13日,新大众文艺座谈会在山东淄博召开,作家莫言、《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新以及众多文艺工作者参加会议。“新大众文艺”从概念提出到引起广泛影响历时不过一年多。
从《延河》杂志的概念阐释中,可以提炼出“新大众文艺”概念的两个核心关键词——数智媒介与大众主体性。从数智媒介的维度来看,概念的提出植根于媒介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网络文学网站等传播载体的全域普及,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工具的快速迭代,共同构建了一个数智媒介深度嵌入大众日常生活的时代语境。这种媒介变革不再是简单的传播渠道更新,而是形成了数字技术、智能工具与文艺主体交互构建的情感表达能量场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撑。与传统文艺创作受制于专业设备、场地资金、技能训练等壁垒不同,数智媒介实现了创作工具的均衡技术赋能:普通人仅凭一部智能手机与简易剪辑软件,借助滤镜、特效等功能即可完成个性化创作;网文创作者可通过对话、接龙等功能实现群体协作;非遗传承人能依托音画融合技术重构传统文化表达空间……这种技术平权为“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奠定了物质性基础,成为概念提出的核心现实依据。
在大众主体性层面,概念的提出精准捕捉文艺权力结构的深层转型。数智媒介的普及使大众在文艺生产链条中的参与度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彻底打破传统文艺的精英垄断格局。创作主体从专业创作者群体转向全民参与的“去中心化”新集群,外卖员、快递小哥、学生、教师、离退休人员等,形成“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的实践图景。更具革命性的是,大众主体性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跨越:网文领域的“本章说”功能让读者直接参与情节设计,短视频的弹幕互动实现创作与反馈的实时闭环,这种“创作即参与”的模式使创作者与受众界限消弭。同时,大众还掌握了文艺评价的话语权,通过点击、转发、评论等行为构建起全新评价体系,使文艺标准从精英判断转向大众共识。
从理论渊源与时代价值来看,“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提出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对中国文艺“人民性”传统的当代继承与创新。它延续了从延安时期“文艺为人民大众”到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却在数字时代赋予其全新形态——不再是精英对大众的“文化给予”,而是大众自主的“文化创造”。这一概念的价值更在于对现实的理论概括:当网络文学、微短剧、纪实短视频等文艺新形态持续涌现,当普通人的个体经验通过文艺创作升华为时代叙事,《延河》杂志提出的“新大众文艺”恰是对这种“多点开花式”文艺现状的精准命名。它不仅揭示了创作主体去中心化、审美表达多元融合的文艺新特征,更指向了一种文化话语权由精英向大众转移的新生态,为理解当代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提供了理论框架。
二、“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溯源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文学杂志始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中提出新的理论概念便是其推动文学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文学杂志提出新的理论概念,并非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行为,其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这与提升杂志自身影响力密切相关。新的理论概念往往具有创新性和独特性,能够吸引读者的关注,引发社会的广泛讨论,从而使杂志在众多刊物中脱颖而出。另一方面,这也是杂志深化介入于当下文学创作程度的重要手段。
如同“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的概念一样,“新大众文艺”中的“新”字意味着这一概念存在一个潜在的相对概念,即“大众文艺”。从新文学发展至今,尚且没有关于“大众文艺”的确切定义。1928年,现代书局创办了文艺类月刊《大众文艺》,郁达夫、夏莱蒂担任编辑,《大众文艺》的名称来源于当时日本流行的杂志《大众小说》。郁达夫在《大众文艺》发刊词中一段话可以看作当时许多新文学知识分子对于“大众文艺”的理解:“我们只觉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回首来看,无论是周作人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提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还是20世纪30年代左联时期郭沫若提出的“新的大众文艺”,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文艺大众化”问题,还是新时期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些理论背后都潜藏着精英知识分子对于普通大众的启蒙意识。
这和《延河》杂志提出“新大众文艺”概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延河》杂志“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提出不再是精英知识分子启蒙普通大众,而是精英知识分子对于当下文艺生态的精确概括,换句话说,即便《延河》杂志没有提出“新大众文艺”的概念,当下的文艺生态已然是大众普遍、深度参与的现实状态。大众不再是文艺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成为了文艺创作和传播的主体,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方式,为文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新大众文艺”概念的再思考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数智时代的到来催生了多样式的文艺形式,“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提出完成了对既有文艺现象的理论追认,但是“新大众文艺”所彰显的大众主体性,是否会撬动新文学以来文艺生态的深层结构?或者说,是否意味着“五四”以来精英启蒙框架的瓦解或者消失?
外卖员的vlog记录、打工者的诗歌创作、非遗传承人的短视频展演……这些来自民间的文艺表达不再需要通过精英话语的“筛选”即可抵达公众视野,传统启蒙模式中“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固定身份边界开始消解。这并不等同于启蒙价值的消亡,而是催生了启蒙形态的转型。当下的启蒙已从单向度的“知识灌输”转向双向互动的“主体对话”。精英知识分子不再是唯一的真理持有者,其创作往往需要回应大众的现实关切才能获得共鸣;而大众的文艺实践也在精英的专业引导中不断提升品质,这种互动构成了“大众化”与“化大众”的辩证统一。作家梁晓声的《人世间》之所以引发全民热议,正是因为它既延续知识分子对时代变迁的深刻洞察,又精准捕捉大众对平民命运的情感共鸣,实现精英思考与大众经验的同频共振。可见,启蒙框架并未消失,而是在“新大众文艺”的生态中完成了从“居高临下”到“平等共生”的重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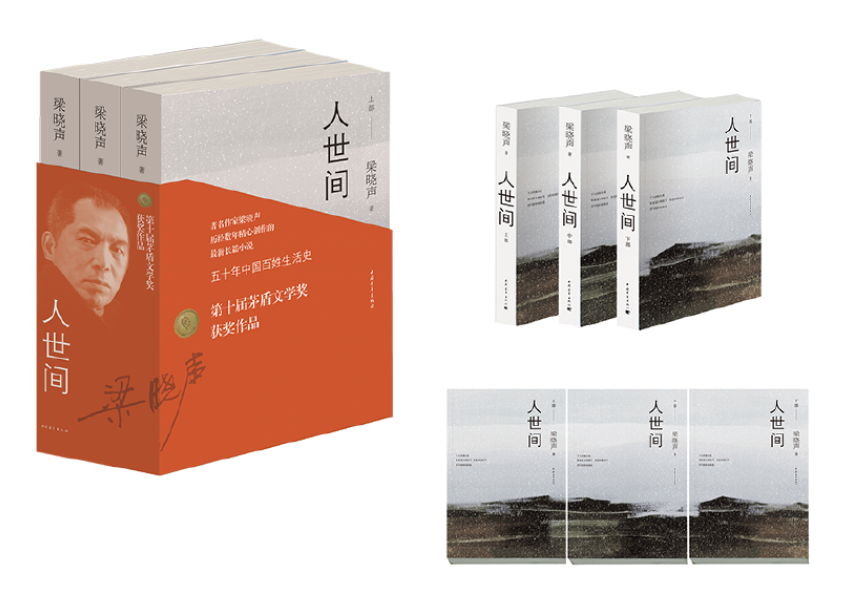
“新大众文艺”所倡导的“大众主体性”,核心是打破创作资格的身份壁垒,但需要注意的是其理论倡导中也在有意淡化专业创作的价值,或者说,这一理论在有意回避探讨“精英/大众”二元对立的模式是否存在。在当下的创作中,精英创作的价值不在于其“身份标识”,而在于其能否为大众文艺生态提供思想养分与审美引领。“新大众文艺”的健康发展,需要精英创作与大众创作形成合力,共同抵御低质化、同质化的侵蚀。
当全民创作成为时代潮流,“新大众文艺”是否会带来对先锋文艺的遮蔽?先锋文艺的核心特质在于其对既有审美范式的突破与对未来艺术形态的探索,往往具有超前性与小众性,而新大众文艺受传播逻辑影响,更倾向于满足大众的即时审美需求,容易形成“流量至上”的评价导向。在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下,实验性的影像创作、晦涩的诗歌表达往往难以获得广泛传播,而通俗化、娱乐化的内容则更容易占据流量高地,这种传播差异可能导致先锋探索陷入边缘化困境。更进一步来说,真正需要警惕的并非大众创作对先锋性的遮蔽,而是商业资本与算法逻辑对文艺生态的垄断,这种垄断可能同时扼杀大众创作的活力与先锋探索的勇气。
跳出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框架,“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还面临着更为根本的挑战。一个是科技伦理的困境。人工智能等技术工具在赋能大众创作的同时,也带来了主体性消解的风险:AI生成文案、算法自动剪辑正在取代部分创造性劳动,长期依赖技术工具可能导致大众创作能力的退化,甚至引发“人的智能被技术替代”的文明隐忧。如何在技术赋能与主体坚守之间找到平衡,成为“新大众文艺”必须面对的课题。另一个是价值引领的缺失。“新大众文艺”的“零门槛”特质使其呈现出泥沙俱下的态势:一些内容为追求流量刻意迎合低俗趣味,背离了文艺的审美使命。“人民大众的创作”不等于“人民文艺”,大众主体性的彰显不仅需要创作权利的平等,更需要价值追求的提升。新大众文艺要实现从“量的繁荣”到“质的飞跃”,关键在于构建良性的价值引导机制——既尊重大众的表达自由,又通过批评评论、平台规范等方式引导文艺创作向高品质、高格调迈进。
理论概念的价值不仅在于概括现实,更在于引导未来。“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提出,为我们理解数智时代的文艺发展提供了重要视角,但它所引发的关于启蒙转型、精英价值、先锋性存续等问题的思考,更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健康的文艺生态从来不是单一形态的独霸,而是大众活力与精英引领、通俗表达与先锋探索、技术赋能与价值坚守的多元共生。
作者简介
潘浩,连云港师范学院教师,文艺学硕士。
来源: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