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综述2】赵建新:《诗学》中的概念范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专家简介】赵建新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戏曲艺术》编审。研究方向为戏剧史论及批评,出版有《中国现代非主流戏剧研究》《戏剧本体与现代审美》《中国戏曲文物图谱》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各类文艺评论逾百篇。文章曾被《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多次转载;作品曾获第二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第三十四届、第三十五届田汉戏剧奖一等奖等奖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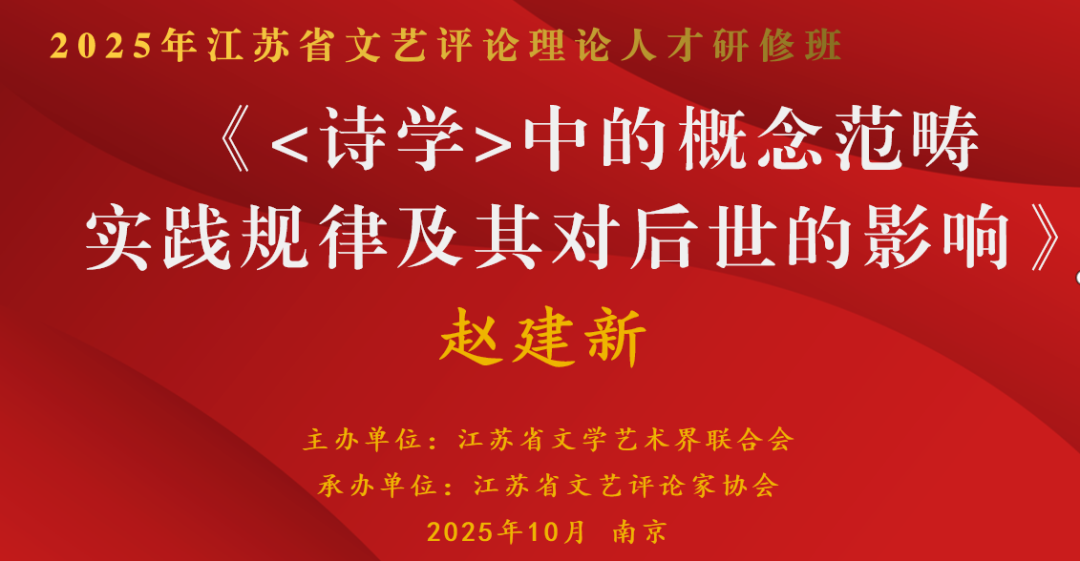
2025年10月19日上午,由江苏省文联主办、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承办的“2025年江苏省文艺评论理论人才研修班”邀请到中国戏曲学院《戏曲研究》编审赵建新老师为学员授课,题为《<诗学>中的概念范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授课主要内容如下:

(理论授课现场)
一、戏剧本体论
1.柏拉图的诗与哲学之争
柏拉图在对话录《理想国》中提出“理式说”与“摹仿说”:“理式说”认为现实世界的本体是理式;“摹仿说”提出艺术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现实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摹仿,因此艺术是影子的影子、摹仿的摹仿。同时,柏拉图认为诗、艺术的创作是虚假的,不是真实的。关于摹仿说,中国古典诗学也有类似的表述,比如李白的《长干行》中提到的“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对游戏的摹仿。
另外,柏拉图从“摹仿说”展开论述悲剧诗和叙事诗,在《伊安篇》《理想国》里提到诗与哲学之争。他认为,戏剧容易引发人的感伤癖和哀怜癖,而理想国里需要的是哲学家和战士,和具有高度理性的人,因此,应把诗人赶出理想国。
2.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
亚里士多德彻底改变了柏拉图的观点,他从正向角度阐释了摹仿说:认为摹仿是真实的,激发出积极、健康的情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列概念。比如“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悲剧的摹仿对象是比我们要好的人——是犯错的好人,其摹仿的媒介是演员,摹仿的方式是动作,摹仿的对象是行动。
并且,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卡塔西斯”的概念,是指通过悲剧等艺术形式,观众内心的恐惧与怜悯之情得到宣泄、净化与升华。其中的“恐惧、怜悯”两个词与古希腊的宗教祭祀、早期城邦民主制密切相关。其实,这些概念也是对古希腊戏剧实践的总结,是建立在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悲剧诗人的创作和丰富的艺术实践之上的。
3.中国古典戏曲与古希腊戏剧比较
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古典戏曲和西方古希腊戏剧源头相似,都融合了诗、舞、乐等元素。首先,两种艺术都要有音乐。例如,古希腊悲剧中就有非常多的音乐成分;其次,两者都有舞蹈,比如出土的古希腊悲剧演员雕塑戴着非常厚重的面具,穿着高底靴,肢体动作有节律。
虽然两者最早的源头都起源于祭祀活动,但是中国古典戏曲成熟形态的出现时间比古希腊时代晚了1500年。从历史发展来看,东方文明是早熟的,但在戏剧的发生学上却是晚熟的。马克思曾用“粗野的儿童”“早熟的儿童”和“正常的儿童”比喻古代不同民族的发展形态。文明形态的产生取决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取决于生产工具,而生产工具的先进和落后决定生产资料,直接刺激国家形态的产生。
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时代,西方人已经发明了铁器。铁制工具提高了生产力,创造出大量的剩余价值。早期的城邦制便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上,而维系共同信仰的意识形态相应而生。由于精神发育和物质生产相匹配,所以马克思把古希腊人称为发育正常的儿童。
中国铁器农具出现在春秋战国,但最早的国家形态却是夏朝。国家形态早于铁器出现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华文明建立在黄河文明基础上,黄河常年泛滥导致土壤疏松,先民们不需要先进的生产工具耕种;二是黄河常年泛滥,先民们必须依靠社会群体的组织形式才能治水。既然东方文明早熟,戏曲在发生学上为什么晚熟呢?研究者证明,中国戏曲产生和佛教的传入有密切联系,是在变文说唱的基础上演化,到了汉唐之后才有了长篇叙事艺术,而这正是戏曲艺术产生的前提。
从美学风格来看,两者也有不同之处。古希腊戏剧写实,是完全代言体的戏剧;中国戏曲写意,融合代言与叙事。以戏曲《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为例,演员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视角,这其实是说书人角色的遗留,因为第三人称叙述脱离了演员的角色主体,类似说书人叙述别人的行动。演员以第三人称视角指引观众,以静观或回首的姿态,一边演一边控制着自己,是叙述者和代言者合一的典型体现。于是,这便造就了两种舞台时空:一个是演员化身于角色正在进行的时空;还有一个是叙述者的时空,呈现出典型的写意形态。
4.诗的真实性
亚里士多德指出,诗人的职责并非描绘已发生之事,而是描述依据可然或必然原则可能发生之事。他认为诗人与历史学家的区别,并非在于是否运用韵文,两者的关键差异在于,历史学家记述已然发生的个别事件,比如阿尔基比阿德斯做过或遭遇过的具体事情;而诗人描述的是可能发生的、具有普遍性的事,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某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基于此,亚里士多德得出诗比历史更哲学、更严肃的结论。
以上的讨论,带来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的思辨问题。历史题材戏剧与现实题材戏剧仅在取材时间上有区别,并无其他本质差异,因此,我们不应将二者的评价标准割裂。面对现实题材戏剧时,评论者不会提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但是会对历史题材戏剧强调此点。历史剧的艺术真实本就包含历史真实维度,无需单独提及历史真实。以刘和平编剧的《大明王朝1566》为例,剧中有“改稻为桑”的情节设计,这一情节虽无历史文献记载,但却符合嘉靖年间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具备历史可能性。
亚里士多德《诗学》提出了“合情合理的不可能”与“不合情理的可能”的观点。戏剧创作应选择前者,也就是现实或历史中未发生但符合艺术必然性与普遍性的内容,而非后者偶然发生的个别事件。因此,当下文艺评论应超越历史实证主义史剧观,不能以“是否符合历史文献的记载”作为历史真实衡量历史剧。历史真实就是通过文献手段不断去澄明,让史实渐次出场和敞开的过程,是动态过程而非静止结果,这个过程具有主客观双重维度。因历史研究主体的背景、经历不同,史料建构会融入主观因素。因此,剧作家选择某一历史人物作为戏剧的主人公,在把握人物个性的前提下,需要把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定性化为特定的情境。人物在特定情境中动机与行动的可能性也正体现历史内在的可能性。而历史内在可能性应是历史题材戏剧的天然基因。
二、戏剧构成论
《诗学》中提及悲剧有性格、情节、戏景等六个组成部分。戏剧情节设计的关键手法是突转与发现。突转,是指遵循可然或必然的原则,使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发现,是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使置身于顺达之境或败逆之境中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仇敌。这两种核心手段运用的精妙程度直接影响戏剧的张力和感染力。以《俄狄浦斯王》为例,剧中人物通过找到牧羊者这一关键情节,实现了“婴儿身份”与“杀王凶手”的双重发现,进而引发命运的重大突转,形成强烈的戏剧冲突与情感冲击。情节的安排围绕行动展开,突转与发现的运用服务于人物命运与情感张力的构建,而“完整性”与“合理性”则是保障戏剧美感的关键。
三、戏剧功能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完美悲剧的摹仿行动必须能够引起恐惧和怜悯。悲剧不应该让一个好人由福转祸或让一个坏人由祸转福,因为圣人和魔鬼都距离普通大众较远,此类形象只会引起公众反感而不能引起怜悯与恐惧。因此,悲剧的主人公一般应为一个中等的人,他们在道德品质上并不是好到极点,只是犯了一些错误而导致灾难,只有这类人才能引起受众内心的恐惧和怜悯。以徐棻改编的《烂柯山下》为例,崔氏嫁给穷书生朱买臣后含辛茹苦操持家务,只是在最一次没有陪主人公朱买臣完成科举,于是朱买臣马前泼水对其极尽羞辱,而完全忘记了前六年妻子所有的辛苦付出。这个改编后的悲剧说出了这样一个人性中的弱点:人最容易记住的是别人对不住自己的地方,却能轻易忘掉别人对自己的好。再比如郑怀兴的《失子记》,这个悲剧在改编时加入了程婴的妻子游玉兰这个形象,描述这位母亲两度失去儿子的悲惨过程,从而让一个被模糊掉、遗忘掉的女性形象重新立体展开,便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看待悲剧的主人公。
赵建新关于《诗学》的授课,深入剖析了戏剧艺术的核心要素。在戏剧本体论中,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论争,到中国古典戏曲与古希腊戏剧的比较,揭示了戏剧的本质与真实;戏剧构成论强调突转与发现对构建戏剧张力的关键作用;戏剧功能论则通过引发恐惧和怜悯,实现对观众情感的触动与升华。这些理论不仅为我们理解戏剧艺术提供了深刻的视角,也为当代戏剧创作与评论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持,启发文艺工作者不断探索戏剧艺术的无限可能。

(理论授课现场)
来源: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