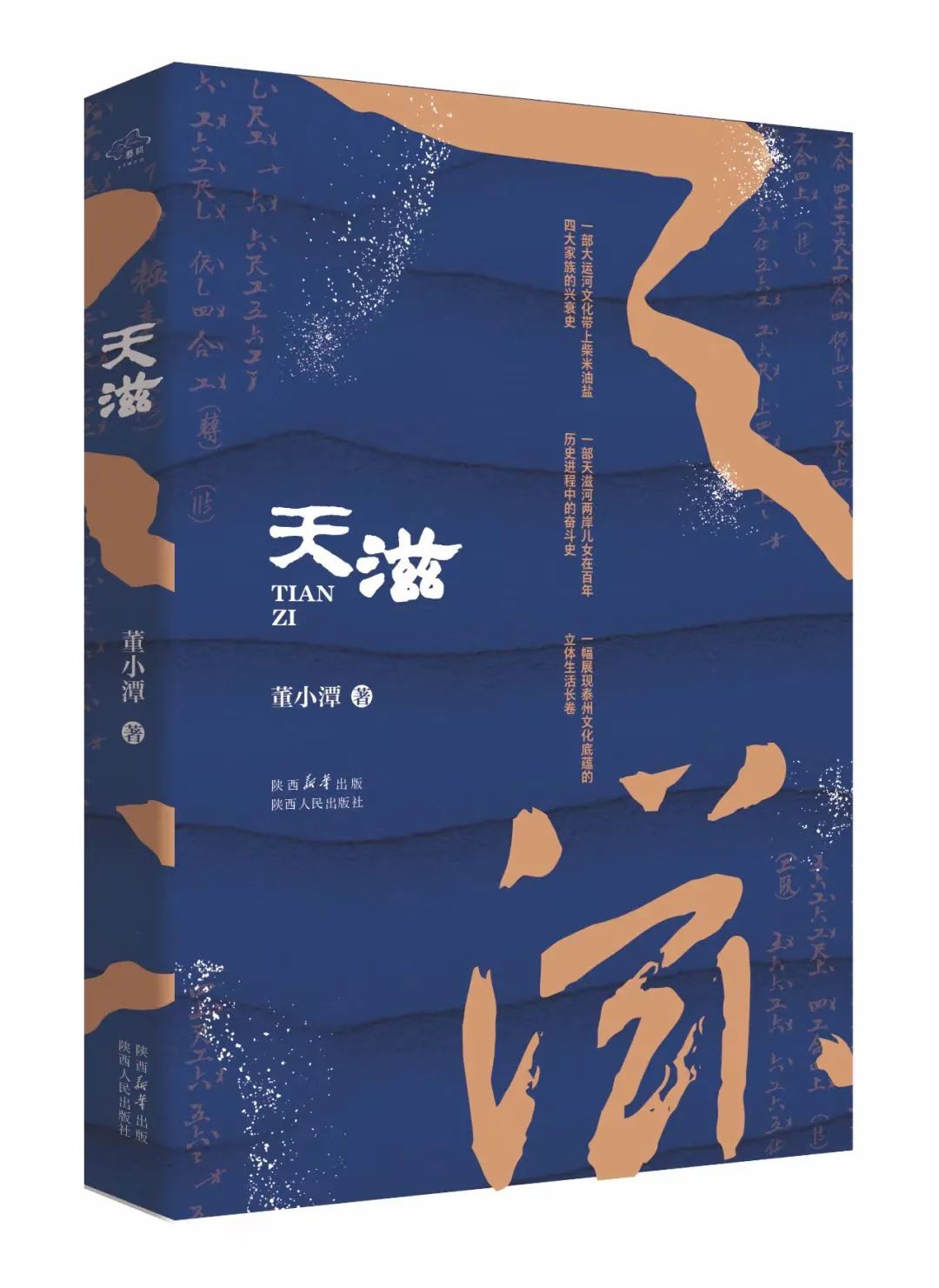
《天滋》的地域书写和空间叙事
—— 董小潭长篇小说《天滋》读札
文 | 薛梅
长篇小说《天滋》以泰州天滋河为纽带,讲述了天滋河两岸柴、米、油、盐四大家族跨越百年的风雨历程和兴衰故事。作家董小潭用了长达8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本近40万字的大书。不可否认,作为一名作家,她是有文学的雄心和野心的,同时她的写作姿态又是笃实和虔诚的,尤其在地域书写和空间叙事上做了积极的探索和成功的实践。
通览全书,显而易见,《天滋》具有鲜明的地域印记。董小潭用“天滋河”来命名这部小说,有“上苍滋润泰州”之意,但其深意不止于此。地处江苏中部的泰州是一座水的城市,江淮海三水汇聚之地。其主城区海陵城自古便是承南启北的里下河门户,如今仍被一条千年护城河环绕着,人称凤城河,“天滋河”即北凤城河,往南是上河,进而通江达海,往北则是下河,有草河、稻河向北流向卤汀河,流向里下河平原更广阔的腹地。泰州还是一座人文蕴藉的历史文化名城,兼容吴楚越之韵,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如泰州学派、戏曲文化、宗教文化、盐文化等。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而文学是照亮灵魂的火炬。董小潭为《天滋》的创作做了充分的文化“考古”,她像一个勘探家,从泰州丰富的文化富矿里,挖掘并撷取了“道教古乐”和“盐”这两个非常具有标识性的泰州文化符号,采用意象隐喻的写法,投射到小说中男女主角身上,一为孟家柴行的孟芊芊,也即后来更名的平安,一名为保护城市文脉不惜以命相搏的献身者;一为经营盐业的高家公子高如风,一名坚定忠诚的革命者。“乐”可视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图腾象征,“盐”关乎城市命脉,则可视为一座城市物质层面的意象代表,“乐”和“盐”双重奏串起全文情节,一座城和一群人的命运紧紧交织,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诚如董小潭在《后记》中阐述其创作思路时所言,“要完整认知一座城市,需将其视为动态的有机生命体——文化是血脉,民俗是肌理,战争是伤疤,经济是骨骼,社会是呼吸。”她在这部小说中分别从文化、民俗、战争、经济和社会等诸多层面来写一座城,同时将四大家族等若干个体的人物命运与城市的发展变迁紧密交织在一起,使《天滋》成为一部个体生命史交织的城市史。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孟芊芊、高如风等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凝练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用一个个“个体人格”来赋予这座城以“集体人格”。作者在接近尾声的《言欢》这章写道:“全城上下如同一块温润的璞玉,外表平和,内里却特别地坚韧。”经过前文足够的叙事和情节的展开,至此得出泰州的精神品格为“温润如玉,外柔内韧、泰然自若”,既是水到渠成,更升华了小说的题旨。
在小说创作中,地域描写不仅是背景的呈现,更是文化、心理和叙事的深层载体。沈从文先生在《湘行散记》的创作谈中强调“地方性”对小说美学的意义,认为湘西的河流与村寨不仅是场景,更是“生命形式的展览”,通过方言、风物构建独特的“抒情共同体”。《天滋》中的地域书写自觉不自觉地遵循或沿袭了这一地域书写的美学法则。在小说中,作者注重铺陈人物所在的环境和场景,且都具有浓郁的地域特征,泰州声腔泰州味。如开篇的《三水》和《庙会》两章中,不惜浓墨重彩,细细描摹了泰州的泰坝盐运、水街相融、市井烟火、美食风物、都天盛会等场景,徐徐展开了一幅天滋河两岸人家的风俗画卷,这些看似闲笔,实为人物的出场提供环境氛围的烘托,为接下来情节的发生做好充分的铺垫,提供必要的载体,也使得小说读起来,时而剑拔弩张,时而舒缓有致,有参差错落之美。
《天滋》的地域书写在表现手法上,没有一味地追求纯文学的写法,而是用“通俗”的现实主义手法写“世俗”,写“风俗”,使作品沾泥土、接地气,雅俗共赏。汪曾祺先生曾经提出“风俗画小说”理论,主张地域描写应“贴着人物写”。在这一点上,我以为董小潭是在向这位里下河文学宗师致敬和学习。小说中民国后期的高福兴、李国香、高二爷,抗战及解放后的孟芊芊、高如风、俞浪行,建设及改革开放时代的俞安然、包良种、俞平凡和高桐等几代人物的描写,作者力求地域描写与人物塑造的贴合度,总体来说人物血肉丰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是成功的。当然,回望董小潭多年的小说创作,我们还可以发现,她一直可贵地坚持现实主义创作路径,这部小说同样如此,小说中所涉柴米盐油这四种物质,均与泰州人一直秉持的“百姓日用即道”一脉相承,这种日常的哲学已经浸淫到泰州人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作者打通了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任督二脉”,虽然主题表达是严肃的,其表现手法与语言风格却吸纳了通俗文学的手法,写的是世俗人情、风俗画卷,作者在二者的融合上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扩大了受众面,使小说气韵生动、雅俗共赏。究其语言风格,有时温婉风雅,有江南水乡的水气,有时又气冲霄汉,有金戈铁马的豪放,掩卷而思,此书常给我一种说书人要拿起醒木惊堂说书的感觉。正如该书首发式上庞余亮先生所言,董小潭的语体是独特的,她吸纳了泰州先贤、评话大师柳敬亭的说书艺术。诚哉斯言,我亦作如是观。追溯董小潭的语言风格,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柳敬亭,甚至“三言二拍”、《水浒传》等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的影响,使得这部小说更接地气,更有韵律、味道。
正如天滋河一样,它的血脉是与长江、黄海乃至更广阔的空间贯通连接的,《天滋》在叙事中没有局限或固着在一个地域空间,而是采取流动的空间叙事法。这一点,恰与法国著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观点颇为一致,他们提出的“解辖域化”理论认为,现代小说中的地域是流动的,去中心化的,反映主体身份的破碎。《天滋》中的空间叙事是流动的,作者没有限于老泰州海陵城范围,而是以海陵这个里下河门户为座标,往南辐射到高港、泰兴、靖江,往东直达姜堰、盐城,这些地域,或长江,或黄海,人物命运的变迁带来人和空间的不断变化,因为人的流动,不断把地域带向新的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使得气象更加阔大和富有变化。当然,不可否认,最广大的区域仍是在里下河范畴,这部小说无疑是里下河文学的新收获。个人认为,里下河文学应当具有更广阔和恢弘的包容性和延展性。值得注意的是,纵览目前我们所见的里下河文学作品,乡村叙事甚多,城市叙事鲜少,而《天滋》却游弋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探寻生命活着的意义,尤其主要篇幅在城市叙事上深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拓宽了里下河文学创作的空间版图。
《天滋》的诞生,是一种执着的双向奔赴。泰州这座城以及她的土地、河流养育了作者,作者便用这本沉甸甸、厚实实的大书,来报答这座城的养育恩情。《天滋》,不妨可视为小说家董小潭试图为家乡写的一本传记,还可以视为,她用8年的光阴,诚意满满的,写给家乡的一份长长的情书。
作者简介
薛梅,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泰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随笔集《何处是归程》《坐看云起时》《一根思想的芦苇》等。
来源: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