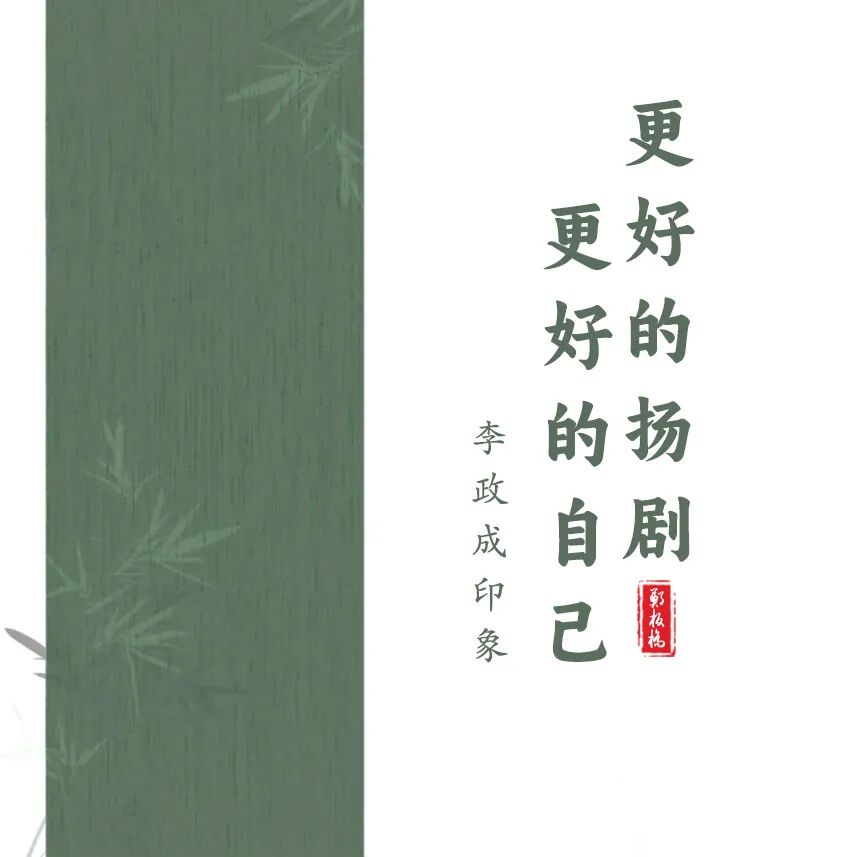

罗 周
剧作家,曹禺戏剧文学奖获得者,江苏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
我见过很多聪明人,而李政成是“笨”的。
他是扬州市扬剧研究所所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扬剧)代表性传承人、新时代中国戏剧(生行)领军人才,不过他是个“笨”的,哪怕天生一张明爽的脸孔。
相识十八年,我们只闲聊过两三次。问到兴趣爱好,他怔住了,愣是回答不上来。我便明白,他热爱的,只有扬剧。
李政成出身扬剧世家,打小跟团辗转乡里。“那时我才六岁,能记得母亲每一次上下场,捧好茶水等着她。母亲卸妆后,都是我帮她卷吊眉带,喏,卷成这么小的一团……”说这话时,他摩挲手指,满脸认真,纯澈的眼神就像个孩子。
聪明人哪会演《汉宫惊魂》呢?不吝血肉之躯,四面八方地狠摔。其中一个转体540°的“僵尸”,硬生生摔折了腰椎。医生担忧他再也站不起来,他则一口咬定:“不会的!”他说:“现在人们介绍我,都说:这是李开敏的儿子;总有一天,他们介绍我母亲,会说:她是李政成的妈妈。”秉持这个念头,他竟坚信自己是摔不坏的。
我见过他的开心、专注,也见过他的失落、愤怒。见过朋友们围坐掼蛋时,他拉过椅子,边看牌边架腿;见过他腿脚受伤时,紧把楼梯扶手一步一挪地上下。半个月后,他“打封闭”主演《不破之城》。那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演出,我坐在前排,见到了他颤抖的、稳定的腿与谢幕时噙在眼中的泪。

世途炎凉,多少人锱铢必较衡量得失、绞尽脑汁谋求“攻略”。李政成呢,依旧“笨笨”地坚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坚信每一次汗流浃背、每一回咬牙椎心,甚至每一束撕裂的肌筋、每一根断裂的骨头,都是一级级台阶,引领他不断向上,在更高处,遇见更好的自己与更好的扬剧。
十二年前,当旁人还在疑惑扬剧能否演出《衣冠风流》这么典雅的士大夫戏时,李政成已坚定地接受了我的文字。那时我没做过剧本阐述,他也没演过同类型人物,可大幕一开,他就是谢安,从容儒雅,浑然天成,给舞台带来了特别的美感。《不破之城》中,李政成饰演史可法,他提枪扎靠、出入万军,又仗剑醉舞,畅抒襟怀。尤其“宴敌”一折,那登楼四望、追昔抚今的恢弘气象与仁心疏阔,让人既痛惜史公之死,又倾慕他如此俊拔地活过,并且,恰似这座“不破之城”,永远活在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之中。
事实上,《不破之城》后的八年,我们各自成长,分别越过了无数个彷徨、疲倦、困惑的时刻,直至2023年再度携手,完成了“古典三部曲”的收官之作——《郑板桥》。那些坚守、不屈与积累,都为这一刻的喷薄。《郑板桥》标志着我的剧本创作从自觉走向自由,也标的了李政成表演艺术的高点,甚至是新时代扬剧艺术的高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只是一部戏,更是一个回答。在我们一次次擦拭泪水、一回回包扎伤口而仍然坚持前行后,上天轻轻递来这份礼物,说:“辛苦了。”
李政成接住了它,人戏合一,臻于化境。

众所周知,板桥一生好画兰、竹、石头,这“三画”正是剧中的华彩段落:“画枷”当街画兰,引动半城围观,李政成文戏武唱、挥洒自若,双手执笔、左右开弓,以大开大合的表演彰显板桥之潇洒狂怪。楔子“放粮”衙中画竹,“一枝一叶总关情”,民生疾苦打在心中、倾于笔下、形于躯体:他以一众遒劲、忍耐、挣扎的形体、造型设计,既体现竹之形态,更体现民众苦难,进而体现人物的苦痛与担当。审美指喻之多重性,极为罕见。到了高潮“石头”画石,人们等待着他将怎样腾挪技巧,李政成却稳若磐石,近乎静态、又酣畅淋漓地完成了五十六句的核心唱段。台上空落落的,只余他一个人;台上又分外“喧嚣”,伴随着艺术家的唱念,红尘过往,自观众心头流过,人世兴衰,都凝聚在他一人身上。
令我感动的,还不止于此。李政成八岁从艺,早年专工武生,后转工文武老生,数十年如一日与髯口、水袖、长枪、靠旗相伴,它们是他张扬表演艺术的重要凭倚。偏是《郑板桥》一剧,传统行头悉数缺位:没有了水袖髯口,失去了靠旗长枪,奇迹般的,李政成完成了他舞台生涯的最佳演绎!究其根本,四十八年的心无旁骛,他终将“自身”砥砺成了程式、打磨成了艺术。举手投足,不假外力,处处在在,活现板桥之寒微、丰裕、穷酸、旷达、烟火形骸、水墨性情……《郑板桥》舞美极简,“归客”“虹桥”等折,表演区近乎空舞台,甚至没有“一桌二椅”做支点。这时,他便是支点本身。他在哪里,戏在哪里,审美就在哪里,那里——便是受众注意力的落点,也是艺术恒久的栖息地。

“京昆打底,剧种立身”,在传承与创新中,李政成不断为扬剧注入规范化、系统化的表演体系,让这门植根于扬州的地方戏曲,拥有了更广阔的传播图景。迄今,《郑板桥》已在北京、上海、香港、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巡演逾六十场,所到之处,反响热烈。他不但带去了“郑板桥”,带去了“扬剧”,更带去了“扬州”。热腾腾的早茶、繁灿灿的虹桥、皎凌凌的明月、纷乱乱的花田,连修脚刀、剃头刀、切菜刀也都入了戏,大俗大雅之间,将一座城的文化记忆,曼妙、温柔、谐趣地传遍四方。
我从没在一个聪明人身上见过这样澄净、猛烈、轻盈又沉重的光芒,是李政成,也是郑板桥,他不“笨”,他也不“糊涂”。他们只是固执地将谋算、取巧、世故、趋奉拒之门外,执着地拥抱赤子之心,如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一样,去追求“千秋不变之人”。当他拼尽全力,接住艺术给予的沉甸甸的“馈赠”时,他也成为了艺术给予这个时代的、沉甸甸的“馈赠”。































